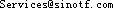| 首頁 | | | 資訊中心 | | | 貿金人物 | | | 政策法規 | | | 考試培訓 | | | 供求信息 | | | 會議展覽 | | | 汽車金融 | | | O2O實踐 | | | CFO商學院 | | | 紡織服裝 | | | 輕工工藝 | | | 五礦化工 | ||
貿易 |
| | 貿易稅政 | | | 供 應 鏈 | | | 通關質檢 | | | 物流金融 | | | 標準認證 | | | 貿易風險 | | | 貿金百科 | | | 貿易知識 | | | 中小企業 | | | 食品土畜 | | | 機械電子 | | | 醫藥保健 | ||
金融 |
| | 銀行產品 | | | 貿易融資 | | | 財資管理 | | | 國際結算 | | | 外匯金融 | | | 信用保險 | | | 期貨金融 | | | 信托投資 | | | 股票理財 | | | 承包勞務 | | | 外商投資 | | | 綜合行業 | ||
推薦 |
| | 財資管理 | | | 交易銀行 | | | 汽車金融 | | | 貿易投資 | | | 消費金融 | | | 自貿區通訊社 | | | 電子雜志 | | | 電子周刊 | ||||||||||
歷史上的河西走廊不僅有“關乎國家經略”的政治意義,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經濟意義也是明顯的。在長期的商業貿易活動中,河西走廊形成了走廊市場體系和“商貿共同體”。同時,還為絲綢之路沿線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河西走廊的重要意義在于,通過市場貿易把走廊內外地區不同民族的民眾長期或者短期地匯聚在一起,實現關聯與互動,進而形成一個“多民族命運共同體”。
每當談到貿易的時候,很多人認為那是商人的事情,與民間普通老百姓少有關聯。其實不然,在歷史上商業貿易與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商貿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的河西走廊不僅有“關乎國家經略”的政治意義,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經濟意義也是明顯的。在長期的商業貿易活動中,河西走廊形成了走廊市場體系和“商貿共同體”。同時,還為絲綢之路沿線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河西走廊的重要意義在于,通過市場貿易把走廊內外地區不同民族的民眾長期或者短期地匯聚在一起,實現關聯與互動,進而形成一個“多民族命運共同體”。
一、陸上絲綢之路貿易中的“胡商” 歷史上的人群移動是復雜的,其中商業貿易利益的驅動是一個重要因素,相當一部分絲綢之路就是由商人開通的。一般情況下,絲綢之路可分為草原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與海洋絲綢之路,河西走廊屬于陸上絲綢之路中的鏈條,而且也是絲綢之路路網中關鍵性的路段。在一般人看來,絲綢之路是單線的,即便是把絲綢之路看作是復線的,最多也關注的是那幾條重要的路線,這其實忽視了絲綢之路最基本的特性。絲綢之路并非單線或者復線的道路,而是由多條主干線路與其他線路連接而成的路網系統。絲綢之路雖然貫穿河西走廊的全境,其實,對于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人群來說,他們所走的具體線路也是不一樣的。河西走廊基本上是一條東南-西北方向的走廊,并不是所有從事貿易的商人群體都從河西走廊的最西端進入,然后經過一段時間的路程之后從最東端走出,或者以相反的方向出入于河西走廊。其實,還有很多的過往客商在河西走廊的南北兩端移動,他們從南北的一些端口出入于河西走廊。

早在絲綢之路之前,歐亞草原與中原地區之間就已經出現了文明的交流。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域地區的“胡商”首先進入河西走廊,然后進入中原地區。不過,當時“胡商”進入中原地區也不排除其他的線路。這里的“胡商”指的是西域一帶的商人,西域在當時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區域,是歐亞地區的一個文明交匯地帶。這里的“胡商”也并非一個明確的稱謂,是對來自西域地區的,在體貌形態、語言特征、宗教信仰等方面與中原地區的人們存在差異的“他者”的一個統稱。其實“胡商”所指的主要商人群體,在不同歷史時段存在實質性的差異,比如有粟特(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回鶻(突厥)商人等。正是這些“胡商”以及中原地區的商人把西域文明甚至歐洲文明,通過河西走廊傳入中原地區,同時也把中原地區的文明傳入西域和中亞。尤其當中原的王朝國家強盛之時,一些西域國家對來自中原的商人與使節非常友好和熱情,來自中原的絲綢、瓷器等幾乎成為西域地區的宮廷用品和上層社會的奢侈品,西域“胡商”攜帶汗血寶馬、琵琶、獅子等西域“珍奇”進入中原地區。隨著絲綢之路上的物品流通,中原王朝的聲譽和影響力也在西域地區的上層社會得以提升,在西域不同地段的部族、國家和民眾也形成了對中原王朝國家的印象、認識和想象。甚至有些時候,西域地區上層社會的官員可能把其他區域的商人誤認為是中原商人而給與一定的“優待”。
曾經有一段時間,“胡-漢”之別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二元結構主義”族群認識論譜系成為中原地區辨析“他者”與“自我”的重要標準。其實,由于“胡人”群體本身是由多個國家、多個地區、多個民族的人群構成,“二元”的核心是多元。在中古時期的漢文典籍中出現了“胡椒”“胡麻”“胡笳”“胡琴”“胡樂”“胡舞”等大量關于“胡物”的記載。其實,這些加了“胡”字的物品未必全部來自被看作“胡地”的西域地區。中古時期還出現了對“胡人”形象的描繪,最典型的就是敦煌壁畫中出現的一些“胡人”畫像。這些畫師可能接觸過“胡人”,也可能“胡人”畫像是純粹出自畫師的想象。總而言之,在中古時期談論或者書寫“胡人”似乎成了上層社會的一種時尚。在有些典籍與圖像中則可能出現對于“胡人”的誤讀,這也體現出了古人的族群邊際意識。總之,我們從這些歷史典籍與圖像留存中發現,當時關于“胡人”的形象既顯示了一種“胡”“漢”之間的邊界,也體現了一種“胡-漢”二元一體的多民族觀念。即便是一種通過想象而建構的族群觀念,也意味著在社會上已經形成了“非單一性”的多民族意識。
在中古時期出現的“胡人”不僅僅指的是某一個族群,而是一個分布地域廣泛、民族成分復雜的群體,包括西域、中亞、西亞、歐洲,甚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群。“胡人”意識是當時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多民族意識,在其背后突顯的是中原王朝國家強盛與開放的態勢、發達的商業貿易,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域內外”互動交流機制。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把作為“胡人世界”的歐亞大陸上所屬不同文化的人群,與中原王朝國家關聯在一起,絲綢之路充當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載體。河西走廊作為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地段或者鏈條,也關乎絲綢之路的繁榮和通暢,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塑與構筑過程極具意義。
雖然河西走廊的長度對于整個絲路而言微不足道,但它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地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河西走廊對于世界貿易體系都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同時也為中原文明和域外文明之間的溝通、交流發揮過顯著作用。
西域作為“文明十字路口”,世界上的諸多文明類型匯聚于此,河西走廊猶如西域地區東段的一個“瓶頸”,是西域文明向東傳播的一個重要通道。正因為絲綢之路的開通,在河西走廊上出現了西域文明進入中原地區或者中原文明進入西域的多個中轉站。在有些歷史時段中,河西走廊是“胡商”的云集區域,如《甘州府志》所載,隋煬帝大業年間,“尚書左丞裴矩駐張掖,掌交市。帝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當今在河西走廊境內的焉支山一帶,還出現了關于隋煬帝時期“萬國博覽會”的傳說。即便這是一種當地人的“歷史心性”,將隋煬帝派朝臣接見西域多國商人作為一種歷史資源來充實文化產業,其背后也說明了河西走廊與西域之間的地緣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開展商貿活動的可能性。粟特商人是“胡商”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古時期粟特商人在中原地區形成了很多聚落。根據榮新江教授的考證,一位粟特康國上層社會的官員曾擔任“甘州刺史”一職,敦煌(古稱沙州)、武威(古稱涼州)曾是粟特人的大本營,武威曾經也是粟特人的一個貿易集散中心。河西走廊不僅僅是一個陸上絲綢之路的通道,在絲綢之路貿易中還充當了西域地區與中原地區之間的過渡帶。走出西域地區的“胡商”群體,有時候在河西走廊滯留一段時間,把西域文明傳播到河西走廊之中。
河西走廊處于地理上的咽喉地帶,絲路上的商貿隊伍一旦繞開河西走廊,進入北面的蒙古草原地區會面臨大戈壁和沙漠,水資源匱乏,走南面則進入青藏高原,復雜的地形影響商路的通暢,高寒的嚴酷氣候影響商人及載貨牲畜的生存。相較河西走廊以南及以北區域而言,河西走廊的海拔相對較低,地勢平坦,水資源充足,綠洲城鎮上還設有驛站,這些條件滿足了商隊的基本需要,還為絲綢之路的通暢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絲綢之路上的商貿活動一直在延續。歷史上,當河西走廊出現割據政權,絲綢之路往往會“繞道”或“改道”,選擇草原絲綢之路等,絲路上的商隊可能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種情況下,河西走廊也會在一段時期內成為一個“死角”,只能等待政治格局的變動與絲綢之路的重新啟動。明朝以來,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嚴重削弱了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性,河西走廊的商路相應地也明顯沉寂了很多。然而,陸上絲綢之路并沒有完全中斷,西北地區由于在地理位置上遠離海岸,一些商品還是在陸上絲綢之路上流動著,也有域外的商人攜帶商品從陸上絲綢之路出入于河西走廊。
絲綢之路上各民族商人的流動,促成了中原商人與“胡商”的互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絲綢之路牽動著跨區域的多民族命運共同體,也是歷史上鑄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重要途徑和載體。作為歷史上陸上絲綢之路組成部分的河西走廊,對于商業貿易中多民族意識的形成,以及多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商貿成為區域文化的“連通器”
商業市場往往是文化匯聚之地,在人類文化的交流中,商貿活動和商人群體扮演了重要角色。河西走廊地處青藏高原、蒙古高原、新疆綠洲、黃土高原這四大地理板塊之間,相應地,河西走廊也就在這些區域文化的“包圍”之中。以上文化區域的相應邊緣一旦稍有伸張,其文化元素就會直接進入河西走廊。通過商業貿易,河西走廊把周邊“四大區域”的文化連通起來,實現了多重文化的匯聚和交融,同時又向周邊區域進行輻射。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河西走廊對于“四大區域”的影響范圍和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最關鍵的因素還是河西走廊本身所產生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這首先就在于河西走廊是否有一定規模的市場,以及其供應的農業產品能否滿足周邊地區畜牧社會的需要。
有些規模比較大的市場是由王朝國家的相關上層機構直接設定的,例如,明、清王朝在河西走廊設置了大型的“貢市”與“互市”,吸引了來自新疆天山一帶、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地區的大量各族商人到河西走廊開展貿易活動,內地商人亦攜帶農耕產品涌入河西走廊,滿足了各方商人的商貿需求。“朝貢體系”是歷史上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與周邊國家和民族地區之間建立的政治秩序體系和互動系統,其中商貿互動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和物質基礎。如地方文獻所記,明弘治二年(1489年)從中亞撒馬爾罕運來的貢品獅子等,進入了作為中轉站的河西走廊的張掖(古稱甘州)一帶準備運往皇都順天府(今北京)。
農耕與畜牧是人類社會的兩大主要生產方式,在此基礎上也形成了兩種文化類型,二者之間屬于互補型關系,尤其體現在各自都需要對方社會的產品,因此商業貿易是實現二者互動的最基本形式。就河西走廊周邊區域來說,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基本上屬于畜牧社會,天山以南的綠洲多屬于農耕區域,但天山以北的大部分地區還是屬于畜牧社會。因此,河西走廊的綠洲農耕社會就嵌合在三大畜牧社會之間,畜牧社會所需農業產品的供給就由河西走廊的市場優先承擔了。歷史上,河西走廊內部的綠洲社會生產一些農耕產品,比如糧食等,但遠遠無法滿足周邊畜牧社會的消費需求。不僅是糧食,畜牧社會所需的大量布匹、茶葉、鐵器、瓷器等物品,都需要從內地運往河西走廊。可見,對于周邊大范圍畜牧社會的需求而言,河西走廊的市場更類似于跨區域商貿網絡的中轉站。支撐河西走廊的畜牧-農耕商貿的,是一個龐大的農耕社會,其范圍從黃土高原的關隴地區到中原腹地,甚至延伸至江南地區。這些農耕區域的產品進入河西走廊,再于此中轉,流入周邊的牧區社會。當然,河西走廊的市場網絡也無法完全滿足如此大范圍的畜牧社會的需求,進入以上這些畜牧社會內部還有很多其他的商貿通道。
蒙古高原位于河西走廊的北面,其西南面的部分地區與河西走廊相接壤。當前作為蒙古高原組成部分的阿拉善高原,與河西走廊的民勤、山丹、張掖、酒泉等地區相連,河西走廊有多條進入蒙古高原的通道。孫明遠、王衛東在本專欄文章《河西駝道最后的駱駝客》中指出:“18世紀中葉清軍平定準噶爾部以后,從中原經由河西到達邊疆地區的商路主要有兩條,一條是經河西走廊過星星峽到新疆,被稱為甘涼大道;一條是經河西走廊東端沿石羊河而下走阿拉善高原,往西過額濟納到新疆,往東到綏遠、包頭、張家口直至北平、天津衛,稱北道。”特別是在駝隊盛行時期,民勤一帶的駝隊極具典型性,其向四周呈網狀分布,來往于農牧區之間。駝隊的商貿運輸勾連起龐大的商業網絡,河西走廊內部的綠洲城市、周邊區域的大城市,甚至內地的大城市都在其中。如此,有大量的農耕產品從河西走廊轉入蒙古高原,蒙古高原西南端部分地區的畜牧產品的一個重要流向亦是經由河西走廊進入中原地區。河西走廊成為農耕商品與畜牧商品的一個中轉站。
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區屬于畜牧社會,盡管其內部也出現了大量出售農耕產品的市場,河西走廊作為中轉市場對青藏高原還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地處青藏高原邊緣的河湟地區,與河西走廊的關系就非常密切,在祁連山脈南北麓之間有一些通道,部分通道還是歷史上重要的“商業大道”,其中扁都口最具典型性。扁都口在文獻中有“大斗拔谷”的記載,蒙古語的意思就是“險要的關隘”。明、清時期,扁都口是從河西走廊進入青藏高原的一條商業主干道,大量來往于河湟地區與河西走廊之間的商人和牧區的牧民,通過扁都口在牧區與農區之間穿梭,進行著商業貿易或者個體性的產品交換。由此,扁都口不僅對于絲綢之路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也實現了青藏高原牧區社會與農耕社會的關聯。在河西走廊的東段,祁連山南北麓之間出現了一些“密集型”的通道,對于來往于這一帶的商人來說,即便對一些小道也是“輕車熟路”。河西走廊的農耕產品沿著一些通道進入青藏高原,同樣,河湟地區的一些畜牧產品也從當地的市場流入河西走廊。明、清時期河西走廊的莊浪(永登)、涼州、甘州、肅州與青藏高原的西寧、丹噶爾等城鎮之間形成了商業網絡,河西走廊的一些城鎮成了商業網絡當中的節點,把青藏高原與天山一帶的游牧社會連接在一起。河西走廊與青藏高原的城鎮之間形成的商業網絡體系,也接通了畜牧文化與農業文化。地處“農耕-畜牧”過渡帶的河西走廊,商業網絡的形成以及通過商業網絡的文化互動是一個重要特性,在其背后也就是畜牧文化與農耕文化之間互補性的連通與互動。河西走廊西段的黨金山口也是河西走廊通往柴達木的一條商業通道。這些重要的商道把河西走廊與青藏高原連接在一起,甚至還是連接中原地區、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重要商路。
蒙古高原與青藏高原是兩大畜牧文化體系,河西走廊正好處于二者之間,在歷史上青藏高原與蒙古高原之間的文化互動中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自1247年“涼州會盟”以來,伴隨著蒙古高原與青藏高原的政治互動的是雙方的商業貿易活動。在商業貿易活動中,多民族的商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推動了商業貿易的順利進行。
天山北部地區屬于畜牧社會,需要大量的農耕產品,但天山南部的農耕產品還是無法滿足畜牧社會的需要,更多的商品還是需要從內地輸入。于是,明、清時期,在河西走廊出現了一些定期和不定期的市場,這些市場吸引了天山北部地區的蒙古人、哈薩克人、布魯特人(柯爾克孜人)與中原地區的漢族商人。這些市場的設立不僅實現了畜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互動,還為天山南北地區與中原的人群接觸與交融提供了保證。
地處不同文化區域邊緣地帶的河西走廊,其聯動起來的跨區域商貿網絡,使得漢族、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哈薩克族等民族的商人和民眾進入河西走廊的市場,實現了多民族之間的交往互動。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民眾對于“異文化”有所認識;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個建構多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實踐場景,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多民族共同體。
三、綠洲市場的商貿網絡與民族互動 河西走廊的平原地帶主要由綠洲和戈壁構成,再加上少量的沙漠。適應耕作的土壤與河西走廊的三大內流河水系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河西走廊歷史上碎片化的綠洲。從明、清直至現代,河西走廊的綠洲面積出現了擴大的趨勢,在一些戈壁地帶還開發了一定規模的農田。這樣,河西走廊碎片化的綠洲也就形成了綠洲連綴體。河西走廊的綠洲分布格局,相應地形成了河西走廊的綠洲商業貿易格局,并進一步形成綠洲貿易體系。在不同歷史時期,河西走廊上綠洲面積的大小不同,走廊東段、中段、西段綠洲城市的規模亦不同,而城市規模和綠洲面積之間關聯緊密。發展到今天,河西走廊的綠洲分布格局已經與歷史上有了較大差距,這種綠洲分布格局及其內部的交通道路體系的變遷,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河西走廊綠洲貿易體系。
施堅雅(William Skinner)曾基于中國四川有關城鎮與村落的調查,提出了“市場理論模式”,探討村、鎮分布格局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為區域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范式。這一“市場理論模式”應用到地處黃土高原的甘肅中、東部地區依然有一定的意義。然而,在河西走廊的綠洲地帶以及綠洲市場格局中,“市場理論模式”出現了部分的“失靈”。首先,地理環境不同,市場體系也就存異。四川成都平原地勢平坦,可耕作土地相對集中,人口密集。而歷史上,河西走廊上的不規則綠洲散布在戈壁中,其人群聚落也與成都平原的聚落有較大差異。在施堅雅的“市場理論模式”中,集鎮并非是均質化的,在大、小集鎮之間還有過渡性的集鎮。而在河西走廊的大集鎮與小集鎮之間,并未有明顯的過渡性集鎮,小集鎮有一種均質化的趨向。河西走廊集鎮的規模主要與兩個因素有關:首先看是否位于綠洲的中心地帶,在歷史上,武威、張掖、酒泉等城市內部都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市場;其次看是否地處交通要道,特別是農耕社會與畜牧社會的交接地帶或者交通要道的出入口附近,比如在清順治年間,今古浪境內的大靖、土門,以及距扁都口不遠的洪水,曾“開市于此”。
河西走廊的綠洲社會是不成規模的“亞綠洲”或者“次綠洲”。每個綠洲內部都有其市場體系,包括了多個不同層級的、大小不等的市場,形成了綠洲商貿圈。大體上,商業貿易規模與綠洲面積呈正比,面積較大的綠洲供養著更多人口、聚落和城鎮,也形成了規模更大的行政機構與貿易體系。
事實上,當下河西走廊的市場格局與歷史上的市場格局相比,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遷。就規模來說,當前的市-縣(區)-鄉(鎮)三級行政結構大體上對應著規模不等的三級市場結構。由行政規劃結合市場本身的發育,過去沒有市場的地方形成了市場,特別是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域出現了集市,而有些曾經商旅云集的重要市場地位不再。在今日的河西走廊上,有些地方市場以“旬”為單位設立集日,每月僅3個集日,這與甘肅中、東部地區高密度的集日形成了顯著差距。在日常生活中,民眾經常去哪個集場主要取決于從村落到集市的距離。基層集市通常設置在政府所在地,大多處于多個村落的中心。其中具有地緣關系的幾個集市形成了“集市集群”。曾經有一段時間,部分行商游走在不同的集市上,或者在特定的“集市集群”中從事貿易活動。一些有實力的商人會從基層的集市進入更高級別的市場。
對于河西走廊綠洲內部的市場體系而言,周邊牧區社會的介入是一個不可低估的支撐性因素。正因為河西走廊綠洲的周邊區域是大規模的畜牧社會,才使得河西走廊綠洲內部的市場貿易有了一定的規模。歷史上的商貿形式一度有“在邑錢,在野谷”的分類,即在農區市場上是貨幣交易,在牧區是物物交易,糧食是農區商人攜帶的主要商品。上世紀50年代之前,在畜牧社會物物交換的貿易形式也是很普遍的,通常外來商品在牧區社會的價格可能遠遠高于其在農區社會的市場價格。
筆者這幾年在河西走廊進行調查發現,歷史上很多牧區社會的各族民眾在農區建立了自己的朋友關系和熟人網絡,最基本的方式是通過“干親”這種擬親屬關系。這種跨民族、跨文化的朋友圈是在當時的社會實踐與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形成的。河西地區的漢人社會有一種普遍的民間認同,認為孩子要想健康成長,就要結“干親”,有時候還會結好幾個。人們還認為,如能結到從事畜牧業的少數民族“干親”,對孩子更吉祥。這種對“他者”的文化認同背后,其實還蘊含著互通有無的經濟關系。有些跨民族之間的交換行為就發生在雙方的家里。很多時候,不管是在市場還是家庭內部的交易行為,都建立在農區社會和牧區社會以“干親”為特色的朋友關系網絡的基礎之上。河西走廊的綠洲市場貿易,為以河西走廊為支點的走廊內外多民族之間的接觸與互動提供了場所,也對農耕區和畜牧區“多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河西走廊內部不但形成了商業網絡,而且河西走廊還起著“聯動”作用,把周邊的廣大地區納入更大的互動網絡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河西走廊具有商業“中心”地位的意義。設立在河西走廊綠洲社會的市場,吸引了河西走廊內部及其周邊牧區社會的多民族民眾,甚至是遠道而來的大量各族商人。河西走廊的綠洲商貿網絡促成了多民族的深入互動,進行商品貿易的不同民族不僅在“自我”與“他者”的交往中建立其認同,更為重要的是,人們也共同促成了各民族互通有無、命運相連的意識。河西走廊的貿易體系形成了一個多民族互動網絡,這一網絡既是一個商貿共同體,又是一個多民族命運共同體。
(本文來源:中國民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