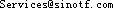| 首頁 | | | 資訊中心 | | | 貿金人物 | | | 政策法規(guī) | | | 考試培訓 | | | 供求信息 | | | 會議展覽 | | | 汽車金融 | | | O2O實踐 | | | CFO商學院 | | | 紡織服裝 | | | 輕工工藝 | | | 五礦化工 | ||
貿易 |
| | 貿易稅政 | | | 供 應 鏈 | | | 通關質檢 | | | 物流金融 | | | 標準認證 | | | 貿易風險 | | | 貿金百科 | | | 貿易知識 | | | 中小企業(yè) | | | 食品土畜 | | | 機械電子 | | | 醫(yī)藥保健 | ||
金融 |
| | 銀行產(chǎn)品 | | | 貿易融資 | | | 財資管理 | | | 國際結算 | | | 外匯金融 | | | 信用保險 | | | 期貨金融 | | | 信托投資 | | | 股票理財 | | | 承包勞務 | | | 外商投資 | | | 綜合行業(yè) | ||
推薦 |
| | 財資管理 | | | 交易銀行 | | | 汽車金融 | | | 貿易投資 | | | 消費金融 | | | 自貿區(qū)通訊社 | | | 電子雜志 | | | 電子周刊 | ||||||||||
作者:付一夫
來源:一夫當觀(ID:ifseetw)
瘟疫,就是我們的影子。
縱觀人類發(fā)展歷程,有很大一部分內容都是人類同瘟疫的斗爭。且不提人盡皆知的歐洲中世紀“黑死病”,單就我國而言,根據(jù)幾千年來古人留下的文獻記載,諸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紅熱、霍亂、斑疹傷寒、傷寒、肺病、麻瘋、瘧疾、吸血蟲病等瘟疫都曾侵襲過這片土地。
也正是由于瘟疫與人類發(fā)展的相伴而行,每當有疫情爆發(fā),人們總是本能地想要從歷史中找尋答案。
其中最值得玩味的,莫過于鼠疫。
公開資料顯示,世界所有國家衛(wèi)生部的文件中,鼠疫都被列為第一號傳染病;在我國,明文規(guī)定的甲級傳染病只有鼠疫和霍亂兩個,而聲名顯赫的非典、埃博拉、禽流感等病毒,都僅僅是被歸于乙級傳染病的行列中。
鼠疫之所以能受到如此高的“待遇”,是因為它著實造了太大的孽。歷史上共出現(xiàn)過三次鼠疫大流行,分別為公元前6世紀(520~565年)、14世紀中葉、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30年代,范圍席卷亞、歐、美、非大陸上的眾多國家,總共奪走了一億多人的生命。這樣的數(shù)據(jù),足以佐證其“瘟疫之王”的地位,很難不讓人談之色變。
19世紀末的香港,正是在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中遭受重創(chuàng)的一座核心城市。
1
史料顯示,自1894年5月10日起,香港居民中開始出現(xiàn)一種奇怪的病,主要癥狀為鼠蹊、腋窩、頸部等處淋巴結腫大,以及發(fā)燒等。當時的《申報》曾連續(xù)多日對此進行報道:
“香港華人,近得一病,時時身上發(fā)腫,不一日即斃。其病起于粵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約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
“……所染之癥皆系兩腿夾縫或兩腋底或項際起一毒核,初時只如蚊蟲所噬,轉瞬即寒熱交作,紅腫異常,旋起有黑氣一條蜿蜒至要害,隨即云亡。”
基于這些較為詳細的記載,不難斷定香港遭受了鼠疫的侵襲,患者癥狀表現(xiàn)正符合了腺鼠疫的種種特點。與此同時,其間香港“疫氣延及鼠子,所斃甚多”,大量的老鼠死亡也是一個重要的佐證。
好好的香港,怎么突然就被鼠疫攻擊了呢?
追根溯源,疫情的源頭在云南。美國著名學者威廉·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曾提到,全球有三處古老的自然疫源地:一是介于印度和中國、緬甸的喜馬拉雅山麓,二是位于中非的大湖地區(qū),三是橫跨整個歐亞大草原、由中國東北到烏克蘭的區(qū)域。而云南恰恰處于第一個疫源地范圍內。澳大利亞學者費克光也在《中國歷史上的鼠疫》中,記載過多起發(fā)生于18世紀中期云南鶴慶等地的腺鼠疫情形。
19世紀起,外國鴉片大量涌入中國,進而帶動了云南居民種植鴉片的泛濫,相對便宜的價格讓產(chǎn)自云南的鴉片很容易在兩廣地區(qū)找到市場。受戰(zhàn)亂影響,廣東的商人迫切希望開辟新的交通路線,此時北海的重要性就日益彰顯。
在此背景下,1876年北海開埠,并早早地出現(xiàn)了汽船運輸,甚至還開設了許多通往香港乃至海外的路線,這讓北海成為云南、廣西以及中南半島客貨運輸重要海路集散地的同時,也加大了疫情擴散的可能性。
果不其然,鼠疫疫情迅速蔓延,廣東南部的廉州、雷州和高州等府在1890年以前已受到傳染;1891年,鼠疫在距離廣州不到300公里的吳川縣流行;1892年4月,廣州爆發(fā)鼠疫,恩平、南海番禺等地亦受到波及……不久之后,香港就出現(xiàn)了鼠疫患者,拉開了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序幕。
鼠疫給香港人民的生命健康帶來了巨大威脅。香港政府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僅1894年,香港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數(shù)為2485人,然而多方面證據(jù)都表明,實際死亡人數(shù)遠不止如此。例如,很多香港居民在患病后,因不愿“客死他鄉(xiāng)”而選擇離開香港回到廣東老家,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在路上就已不治身亡,這些都未納入香港的官方統(tǒng)計。
在此期間,港人懼鼠疫若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及,大量人口紛紛逃離香港,共計約8萬人,幾乎占當時香港總人口的1/3,而香港的商業(yè)也因此而凋敝,市面蕭條,工作乏人,全然不復此前的繁榮盛景。
此后多年,香港依然深受疫情困擾,主要原因在于技術手段所限,當時還沒有治療鼠疫的特效藥,現(xiàn)代西醫(yī)治療鼠疫所采用的抗生素如鏈霉素、四環(huán)素、氯霉素、磺胺類藥物等特效藥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才發(fā)明的,而鼠疫疫苗中的減毒活菌苗到1908年才開始使用,它對腺鼠疫有著較好的免疫力,不過對肺鼠疫效果欠佳,但也足以讓香港在1909年以后的發(fā)病率明顯降低,這已是后話。
2
面對疫情的來勢洶洶,當時的香港政府迅速地審時度勢以采取應對措施,而他們的努力也著實收獲了不小的成效。
具體而言,香港政府主要從兩個方面予以統(tǒng)籌協(xié)調:
其一,出臺《香港治疫章程》,將疫情通告全港居民。
1894年5月10日出現(xiàn)首例鼠疫病例之時,政府便知此事非同小可,隨即馬上召集各部門集會商討,進而制定出了《香港治疫章程》,作為綱領性文件來指導整個香港治疫事宜,該文件刊登在5月12日的《香港政府憲報》上,其中幾條關鍵內容如下:
凡有人在港內或別處來港患疫斃命者,其尸骸須在本局所定之專處埋葬,至埋葬如何慎重之處,仍由本局隨時諭行;
凡人知有人患疫或類似疫癥者,須即赴最近之差館或官署報明,將情照轉會局,以便辦理;
凡患疫之人遷徙醫(yī)船或別限所,本局委有人員辦理,如非有本局或本局所委之員及奉有執(zhí)照醫(yī)士之命,不得擅行遷徙,既經(jīng)奉命,其遷徙應如何慎重辦理,仍由局隨時諭行;
凡在有疫鄰近及本局所定界限地方,本局時委人員逐戶探查,以視屋內情形果否清潔,并查有無患疫或由疫致死之人,如屋內污穢不潔,該員即飭令由本局所委之接攬灑掃人夫洗掃潔凈,灑以解穢藥水,務期盡除穢惡,如屋內查有尸骸,則立即將其移葬,倘有患疫之人,則如例遷徙醫(yī)船或別限所調查。
從發(fā)現(xiàn)首例病患到制定出周密的治疫章程,香港政府僅用了一天的時間,反應之迅速令人贊嘆。而從該文件的內容上看,同樣較為完備系統(tǒng),這使得香港的救治工作有了明確的指導,對于最終控制疫情意義重大。
與此同時,香港政府還格外重視危機爆發(fā)時的信息溝通,通過政府公告和各路媒體來向全社會發(fā)布病疫情況。
例如,政府部門先后在5月11日、5月29日、5月31日、6月9日、6月23日和8月28日發(fā)布公告,及時與香港居民進行溝通,尤其是在5月29日,香港總督羅便臣正式宣布香港為疫區(qū),并告知民眾,政府已采取有效手段隔離與醫(yī)治病患,著力破除謠言,消除大眾恐慌情緒。
再如,自5月5日起,香港《申報》就肩負起了及時通報香港疫情的重要任務,其中5月報道疫情11次,疫情高峰的6月幾乎是每日報道,7月報道13次,如此高效的報道離不開香港政府的有力支持。
事實證明,由于信息透明度極高,各種謠言和留言不攻自破,民眾的情緒得到了極大穩(wěn)定,相關的應對措施也就變得格外高效。
其二,想方設法救治染疫病人。
對患者實行隔離治療成為各方共識,然而,當時香港的醫(yī)院并沒有針對傳染病的病房,床位數(shù)量更是有限,再加上患者人數(shù)實在太多,使得醫(yī)院無計可施。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政府下令將灣泊在港內的輪船“夏珍尼亞號”作為臨時的隔離醫(yī)療場所,但凡感染鼠疫的病人都要送到該船接受西醫(yī)治療,從而緩解了醫(yī)院的壓力。
不過,由于鼠疫傳播速度極快,患者數(shù)目與日俱增,而香港的醫(yī)護人員有限,分身乏術。為此,香港政府多次向外埠請求援助。據(jù)當時《申報》刊載:“……新患疫癥者有48人,染疫而死者76人,在港醫(yī)生不敷診治,是以請上海工部局延聘醫(yī)生六人附船前往,分派醫(yī)院醫(yī)船,俾病者得以藥到病除”,“英官致電駐日之英國水師提督,欲延聘西醫(yī)來港,藉以診治”。這些都是救助病患、抑止疫情進一步蔓延的正確途徑。
除了上述兩方面之外,香港政府還及時封鎖了疫區(qū),主動搜查隱藏的患者。對于可疑病人進行觀察,對于暫時不能確診的患者,則由士兵看管,以免隨處走動擴大傳染。同時,各部門還著手對疫區(qū)進行消毒清潔,人手短缺時,港府從部隊調來幾百名士兵一起檢查疫區(qū)并進行消毒工作。這些工作人員“當疫癥初起時,差役查搜屋不遺余力,竟有終日奔走越十點鐘之久或十五點鐘之久而未得稍息者”。也正因為如此,疫區(qū)的環(huán)境得到了迅速改善,并較為有效地切斷了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對于最終控制疫情起到了關鍵作用。
上述實踐也為中國其他疫區(qū)提供了極佳的參考范本。
3
瘟疫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深刻的,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也能促成人類自省,由此引發(fā)一系列變革,并推動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盡管這種作用并非來自于人們的主觀意愿,而是基于生存的本能。
當鼠疫得到控制之后,為了防止悲劇重演,香港政府痛定思痛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
比如,他們組織各方專家進行了鼠疫專項研究,積極探索病源、了解病因,其中以法國傳染病專家亞歷山大·耶爾森和日本的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最為知名,他們證明了香港爆發(fā)的鼠疫多為腺鼠疫,耶爾森還由此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發(fā)現(xiàn)鼠疫病原體的學者;另外,英國皇家內科醫(yī)師學會會員、醫(yī)學博士辛普森赴港對疫情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后,提交了一份《香港鼠疫爆發(fā)和長期流行的原因與治療方法建議的報告》,其中對香港鼠疫長期存在和反復發(fā)病的原因做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并提出可行性建議,影響深遠;
再如,香港乃至全中國,都逐漸建立起了近代意義上的鼠疫應對機制,并開始全面接受與采用西方的醫(yī)療技術,以及加強城市基礎衛(wèi)生設施的建設,使鼠疫這一曾經(jīng)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傳染病得到有效整治,而人類發(fā)展史上也終于出現(xiàn)了對抗鼠疫的勝利曙光——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幾乎再也沒有爆發(fā)過大規(guī)模的鼠疫。
這場發(fā)生于香港人與鼠疫之間的“短兵相接”,是全人類與瘟疫的斗爭史上,極為閃亮的一筆。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盡管已是126年前的事情,但至今仍極具教育意義。
而今“妖霧”又重來,可這次絕不一樣。我們必須認清的事實是:此刻的疫情,要遠遜于126年前的香港鼠疫,而中國的經(jīng)濟實力、醫(yī)療技術、防疫條件和動員能力,卻又遠勝于當年。更何況,“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歷來都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不管任何的艱難險阻,我們都因這樣的團結一心、勇敢拼搏而挺了過來。
這是我們最大的資本和底氣所在。
新春佳節(jié)已至,春天的腳步漸行漸近,而新春孕育著生機,新年亦承載著希望。
盡管過程可能并不容易,但最終結局如何,你我都應該堅信不疑。
參考文獻:
1、 彭海雄,《1894年香港鼠疫研究——基于19世紀香港社會變遷的考察》,2005;
2、 崔艷紅,《19世紀末20世紀初香港鼠疫與港英政府的應對措施》,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