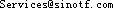| 首頁 | | | 資訊中心 | | | 貿金人物 | | | 政策法規 | | | 考試培訓 | | | 供求信息 | | | 會議展覽 | | | 汽車金融 | | | O2O實踐 | | | CFO商學院 | | | 紡織服裝 | | | 輕工工藝 | | | 五礦化工 | ||
貿易 |
| | 貿易稅政 | | | 供 應 鏈 | | | 通關質檢 | | | 物流金融 | | | 標準認證 | | | 貿易風險 | | | 貿金百科 | | | 貿易知識 | | | 中小企業 | | | 食品土畜 | | | 機械電子 | | | 醫藥保健 | ||
金融 |
| | 銀行產品 | | | 貿易融資 | | | 財資管理 | | | 國際結算 | | | 外匯金融 | | | 信用保險 | | | 期貨金融 | | | 信托投資 | | | 股票理財 | | | 承包勞務 | | | 外商投資 | | | 綜合行業 | ||
推薦 |
| | 財資管理 | | | 交易銀行 | | | 汽車金融 | | | 貿易投資 | | | 消費金融 | | | 自貿區通訊社 | | | 電子雜志 | | | 電子周刊 | ||||||||||
新結構經濟學
對于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投入,是否能夠推動發展中國家高速發展?一個成功的例子是,中國1997、1998年實施一輪積極財政政策以來,高速公路從4700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25000公里,在獲得豐厚回報的同時,也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要讓這一經驗的共享可行,我們就要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前景做出判斷。我在赴任世行之前做過很多相關研究,從數字上看好像很悲觀。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后的1950年到2008年,全世界僅有28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水平與美國的差距能夠縮小10%以上,其中僅有12個不屬于歐洲國家或出產石油、鉆石的國家,而且這12個經濟體大部分位于東亞。除此以外,全球其他150多個國家都陷入了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為什么有那么多國家會陷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所有發展中國家應該都有潛力得到快速的經濟發展,因為經濟增長的本質,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的過程,這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樣適用。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還具有后發優勢,所以其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的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快兩三倍,如果發達國家平均增長速度是3%,發展中國家就有可能是9%。為什么此前發展績效欠佳?中國有一句話叫做“思路決定出路”,問題就是,發達國家提出的發展理論給予了發展中國家錯誤的指引。
我們知道,發展經濟學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才從現代經濟學中分立出來的新學科。第一波發展經濟學理論結構主義,主張進口替代戰略,即認為發展中國家要追趕高收入的工業化國家,必須發展那些發達國家具有戰略優勢的現代產業。而由于市場失靈,發展中國家只能依靠政府主導的方式,才能建立現代化的產業。比如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推行的超英趕美戰略。
但在實踐中,這一戰略的推行效果非常差。遵循該戰略的國家在初期取得了部分投資拉動的成效,但很快就遭遇不斷的危機和經濟停滯。進入20世紀80年代末,發展經濟學思潮發生改變,認為發展中國家缺乏發達國家現代化的市場機制和市場配置效率,因此提出了“華盛頓共識”,即主張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但實際的推行效果比原來更加糟糕。從統計數字來看,發展中國家經濟在20世紀80~90年代的增長速度比60~70年代還要低,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更高。按照那些理想模式推行的國家,比如蘇聯和東歐,最終經濟崩潰,陷入長期停滯,而其他發展中國家則出現了所謂的“迷失的20年”。
相反,那些成功的國家卻是與這些理想模式背道而馳的。在20世紀50~60年代大家主張進口替代的時候,成功的發展經濟體都是出口導向,而在20世紀80~90年代大家談休克療法的時候,中國、越南推行的卻是雙軌制。當時學界有一個看法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全世界最糟糕的就是雙軌制經濟,結果卻是中國經濟獲得了30年的高速增長。
所以,當前的發展理論應該反思,為什么那些實施了“錯誤”政策的國家在實踐中獲得了成功,而遵循“正確”政策的國家反而發展得一塌糊涂。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現在的發展理論沒有真正了解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不僅是資源的最優配置,其本質是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的不斷升級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必然存在市場失靈,因而需要由政府給予有效的引導和支持。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由于比較優勢不同,產業結構也不同。如果讓資本稀缺的發展中國家去發展發達國家的優勢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必然只能依靠政府來保護補貼,實施效果肯定很差。1980年代中國推行市場化改革,固然存在很多扭曲,但那是因為此前全面推行趕超戰略造成的結果;如果沒有解決根本問題而直接去除扭曲,那些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必然都會倒閉,進而會造成經濟的崩潰和社會的不穩定。
很多人認為經濟學理論應該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但《國富論》只是簡稱,書的全名叫做《對國民財富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只是結果,關鍵是其“性質”和“原因”的探索。《國富論》出版于1776年,而工業革命則是在18世紀中葉發生的,也就是亞當·斯密在寫《國富論》的時候,工業革命剛剛萌芽,事實上亞當·斯密并沒有看到工業革命。因此,在《國富論》中,假定了技術和產業是給定的,在此情況下,依靠“看不見的手”可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但是,自亞當·斯密到現在,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什么?資源配置當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結構的不斷變遷,而結構不斷變遷必然存在市場失靈的問題。
因此我們現在應當考慮的是如何創造條件,讓各個國家在每個發展階段都具有競爭力,并依靠競爭力積累資本,作為產業技術升級的基礎。我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倡導這個觀點,這與過去的理論在邏輯和哲學觀上有很大不同。過去的發展經濟學基本上都是以發達國家作為參照系,來看發展中國家缺少什么或是哪方面做得不好。我認為應該反過來,發展中國家應重點關注自身擁有什么要素,以及在此要素稟賦下可以做什么,即自身的比較優勢是什么,而政府應該幫助企業將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做大做強。
如果各發展中國家能夠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充分利用后發優勢,應該可以達到20-30年甚至更長時間8-9%的增長,從而在一代人之間從低收入國家變成中等收入國家,在兩代人之內變成高收入國家。即便是在當前相當不利的國際金融經濟環境當中,發展中國家還是有很多機會可以保持強勁的快速增長。比如,中國大陸現在雇傭的制造業工人共有8500萬人,而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的制造業工人只有970萬,韓國在80年代是230萬人,臺灣則不到200萬人,香港是100萬人,新加坡是50萬人。目前,中國初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已經超過每月2000元人民幣,即350美元/月。我相信十年之內工資水平會增加到1000美元/月。所以,這些勞動力密集的產業會像20世紀60年代由日本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再由亞洲四小龍在80年代轉移到中國那樣,也會逐漸從中國轉往海外。如果我們沿著正確的發展思路制定政策,掌握新的機遇期,我認為所有發展中國家應該都可以進入到快速發展的工業化階段。
重構國際貨幣體系
這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最根本的原因是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缺陷,即以國家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從而使得美國可以通過印鈔增發貨幣,長期支撐其貿易逆差與財政赤字。在國際貨幣理論中,“特里芬悖論”提出,為滿足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增長之需,美元的供給必須不斷增加,從而使得美國擁有的黃金的增速低于美元供給的增長,進而使得國際貨幣制度的基礎發生動搖。實際上這只是一個理論上的可能性,真正造成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和這次金融危機爆發的不是“特里芬悖論”,而是美國過度的財政赤字。20世紀60年代,在越戰已造成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美國總統約翰遜提出“偉大社會”的施政目標,大幅增加社會開支,造成美國巨大赤字,進而導致黃金儲備不足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也是由于美國財政赤字加上家庭赤字造成的,而非“特里芬悖論”。
如果這場世界金融經濟危機不能快速走出去,美國國力一定會越來越受到削弱。美國GDP占全球GDP比重,從2001年的32%一路降至現在的23%,而中國的GDP占全球GDP比重則在不斷增加。在這種狀況下,世界很可能進入一個多元化的儲備貨幣體系,包括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英鎊、瑞士法郎等儲備貨幣。其中重要的儲備貨幣有三種——美元、歐元和人民幣。
這樣一個多元化的儲備貨幣體系是否穩定?現在國際上通行的認識,是覺得這樣的國際貨幣體系比較穩定,因為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的沖突是導致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不穩定的原因,而在多元貨幣競爭的情況下,如果一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缺乏自律,市場就會拋售該國貨幣,從而導致其失去儲備貨幣地位,而各儲備貨幣國家為了維持其儲備貨幣的利益,也會比較謹慎。
我個人的看法恰好相反,因為競爭、自律的前提是這些國家的經濟運行健康。而在未來十年、二十年,這些發達國家都還存在很多硬傷,很多結構性調整根本無法完成。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也必然存在體制性的缺陷。在國際流動性過剩、短期投機套利受到鼓勵的情況下,我們會經常看到國際投機家唱空這個國家、唱多那個國家,大量資金流入被唱多的國家,一個結果是導致這些國家產生房地產泡沫、股市泡沫,第二個結果就是使得這些國家匯率大幅升值,競爭力下降,加劇泡沫程度,而這時國際炒家又會說這個國家經濟不可支撐,開始唱空這個國家,唱多另外一個國家。最后,很可能會演變為各個國家輪流做莊。這可以給國際炒家帶來很多機會,但會給這些儲備貨幣國家帶來很大沖擊,使得國際貨幣體系更加不穩定,并進而造成對非儲備貨幣國家的更大傷害。
所以在此狀況下,我們應該認真反思全球貨幣體系。周小川行長呼吁IMF擴大特別提款權,獲得國際上很多人的支持,但是我認為這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因為特別提款權背后還是主權貨幣,主權貨幣的基礎不牢,在此之上建立的大廈肯定不穩固。所以,我建議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凱恩斯提出的“班克爾”(bancor)的改進版——“紙黃金”,來作為全球儲備貨幣,替代目前的國家儲備貨幣,同時保留每個國家的貨幣,以固定匯率和“紙黃金”掛鉤。
“班克爾”是以黃金或者一攬子大宗商品作為基礎,而我現在提出的“紙黃金”是完全信用貨幣,它具有黃金的特性,但又可以避免黃金的弊病,因為它是按照弗里德曼提出的“k比例法則”發行,即可以根據經濟增長的需要來增長。這種超主權的貨幣,可以避免用國家貨幣作為儲備貨幣所帶來的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的沖突。同時,保留了各個國家自己的貨幣,使其擁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避免目前歐元區發生危機的國家沒有自己的貨幣,不能貶值的弊病。
實際上凱恩斯當時提出的“班克爾”,在理論上比用美元做儲備貨幣更具優勢,但為什么沒有被采納?我認為有兩方面原因,當時美國經濟總量占全世界比重超過50%,而且那時美國經濟充滿了生機和活力,大家對美國經濟很有信心,所以一方面美國不愿意放棄國際儲備貨幣的利益,二是大家認為這樣的安排比較方便。但是現在不同,美國總量占全世界比重已經降至23%,十年之內一定會低于20%,而不論美國、歐洲、日本,各自經濟都存在問題,而中國目前還是發展中經濟體。所以多元化儲備貨幣體系可能會很不穩定,這對儲備貨幣發行國和非發行國都不利。因此,我認為類似“紙黃金”這樣的超主權貨幣,對所有國家而言將是消除不穩定的共贏選擇。
力推“從西潮到東風”
我的新書起名為《從西潮到東風》有三個原因。首先,長期以來,發達國家的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也同樣認為,發達國家有一套完善的理論和完善的體制,發展中國家只要將其掌握并應用到發展中國家,按此作為樣板來實踐,就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但是,從這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中我們認識到,發達國家并沒有完善的理論,也沒有完善的體制,這場危機西方世界基本上沒有預測到,而在危機爆發之后也提不出有效的對策,所有出臺的政策都是滯后的。此外,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很多經濟學家因提出發展理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他們給發展中國家開出的藥方是無效的。所以,在這種狀況下,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非常需要進行理論創新。發展中國家要真正把握自己的命運,必須了解自身現實,以及要解決的問題本質,并發現機遇與限制條件,自己來發展理論。
其次,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GDP在全球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在國際經濟板塊與權力板塊轉變過程當中,一定會有很多矛盾和沖突。如何來解決這些矛盾和沖突?中國有一句話叫做“理直才能氣壯”,如果理不直,即便我們是做正確的事情,也會氣不壯,使我國在國際場合經常只能按照別人的音樂跳舞,處處處于被動地位。比如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在國際貿易不平衡的討論當中,國外的理論一致認為問題出在東亞、出在中國就是一個例子。
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后,東亞很多國家增加外匯儲備和出口,學者可以很容易構建一個模型說明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出于自保的動機,但這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方面。有些人可能知道真正原因,但是出于政治需要,“指鹿為馬”,但是,更多學者是“瞎子摸象”,只看到表象,沒有抓到問題的本質。“指鹿為馬”加上“瞎子摸象”,必然會造成“眾口鑠金”,因此使得我們在國際談判上一直處于被動地位。盡管我們可以不去理會這些爭論,埋頭做自己的事情,但這終究不是辦法。所以,我們非常有必要自己進行研究,去了解問題的本質。我們身處發展中國家,除了可以看到發達國家提出的問題,還可以看到他們看不到的現實,這樣可以使得我們能夠提出更全面的理論,來把各種現象解釋清楚。比如要解釋這次全球金融經濟危機,我們不僅要看到中國的大量外匯儲備用于購買美國國債,還必須要了解到,除了中國與東亞經濟,美國之外的很多發達國家同樣也是貿易盈余,外匯儲備大增,就連拉丁美洲國家也由過去外貿赤字轉為了盈余,而且國際經濟進入加速區并非僅靠中國的外匯儲備,即便是三萬億的規模,與全世界總額相比也是很少的。只有把這些講清楚,中國才能在國際舞臺上化被動為主動。
最后,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目前僅為5400美元,按照購買力平價接近10000美元,與美國的48000-50000美元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作為轉型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必然有很多體制、機制的問題,需要解決。但是,中國的社會與知識分子不能只停留在作為批判家的層面。要做批判家很容易,只要拿一個理想模型與現實比對,都可以下結論說現實不是理想的安排。但是,理想模型不能作為藥方,我們必須要了解問題產生的原因、歷史及現狀,了解問題是內生還是外生的,以及解決問題有什么有利和不利條件,如何來發揮有利條件、克服不利條件。這樣才有辦法在未來20年、30年繼續保持比較快的增長。
我長期持有一個觀點——中國未來20年還有維持8%的增長潛力,很多人表示質疑。但是我們要看到,經濟增長的本質是技術的不斷創新、產業的不斷升級,中國現在正處于日本1951年的水平、新加坡1967年的水平、臺灣地區1975年的水平、韓國1977年的水平。在同樣的水平上,這些國家和地區利用后發優勢可以維持20年8-9%的增長,為什么中國會不具備8%的增長潛力?盡管我們當前存在不少問題,但是日本、臺灣、韓國那時也都存在問題。我們要了解問題是怎么產生的,哪些是可控的,如何推動增長為未來創造更多條件和機遇,這樣才能推動中國在未來十年到二十年獲得一個比較穩定的快速增長。
同時,這還不只是為了中國,而是為了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民族主義風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擺脫殖民地的發展中國家紛紛開展建設,他們遵循的大部分是西方的理論,導致的結果卻都是屢受挫折。我們作為中國這個最大、最有動力的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總結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不僅能幫助中國制定未來20年、30年的發展道路,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會有很大的幫助。我認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是人均收入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而應該是全面的復興,包括思想意識形態的復興。我們有責任去了解現實,提出新的理論和新的思想,推動新的思潮,這樣才能真正幫助中國完成現代化,也可以幫助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那樣才是中華民族的真正的偉大復興。我將這本書起名為《從西潮到東風》,就是希望鼓勵大家一起朝這個方向努力。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本文為作者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第66期“雙周圓桌”內部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由論壇秘書處整理,經作者審核。本次研討會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與交通銀行共同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