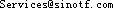| 首頁 | | | 資訊中心 | | | 貿金人物 | | | 政策法規 | | | 考試培訓 | | | 供求信息 | | | 會議展覽 | | | 汽車金融 | | | O2O實踐 | | | CFO商學院 | | | 紡織服裝 | | | 輕工工藝 | | | 五礦化工 | ||
貿易 |
| | 貿易稅政 | | | 供 應 鏈 | | | 通關質檢 | | | 物流金融 | | | 標準認證 | | | 貿易風險 | | | 貿金百科 | | | 貿易知識 | | | 中小企業 | | | 食品土畜 | | | 機械電子 | | | 醫藥保健 | ||
金融 |
| | 銀行產品 | | | 貿易融資 | | | 財資管理 | | | 國際結算 | | | 外匯金融 | | | 信用保險 | | | 期貨金融 | | | 信托投資 | | | 股票理財 | | | 承包勞務 | | | 外商投資 | | | 綜合行業 | ||
推薦 |
| | 財資管理 | | | 交易銀行 | | | 汽車金融 | | | 貿易投資 | | | 消費金融 | | | 自貿區通訊社 | | | 電子雜志 | | | 電子周刊 | ||||||||||
2008年6月我接受任命,到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履新之前,我對未來四年想達成的目標有所準備。2007年,我曾經在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上發表演講,就我對經濟發展和轉型成功或者失敗的原因、一個國家如何加速其現代化等的思考,做了詳細的闡述。世界銀行是國際上最為重要的多邊發展機構之一,其首席經濟學家的工作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貧困、尋找走向繁榮之路。接受世行的任命,我希望能在這個平臺上,繼續將我的觀點與學界進行交流,并希望利用此平臺,幫助發展中國家克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瓶頸、障礙,實現國家的現代化。
經過四年的交流,我的這一認識更為深入,同時我也更有信心。四年后,我帶回了兩本書,一本是《新結構經濟學》,就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發展政策提供一個反思的理論框架;另一本是《繁榮的求索》,這本書闡述了“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觀點,并與我在世行作為首席經濟學家四年的工作經驗進行了結合。
到世行之后,有些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全球金融危機突如其來,這場危機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大、最嚴重、涉及面最廣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2008年6月我抵達華盛頓的時候,全世界關注的焦點還集中在糧食價格、石油價格的飛漲,以及如何治理通貨膨脹,如何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這種輸入型通貨膨脹給其發展帶來的挑戰。我向同事提出:在通貨膨脹得到遏制后,接下來是否會發生通貨緊縮?大多數人對這個問題不以為然,因為他們相信的是“大緩和”,認為發生通貨緊縮是無稽之談:基于此前20年的成功經驗,歐美發達國家的政府都認為,他們已經能夠嫻熟地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平緩經濟的周期波動。不幸的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治理通貨緊縮成為各國政府面臨的挑戰。
其實,在危機爆發之前,我們對此也有過一次討論。每年8月底,美聯儲都會在懷俄明州杰克遜霍爾召開年度會議,邀請全世界最頂級的銀行家、金融學家參加。2008年會議期間,我應邀去參加世行前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在其莊園舉辦的小型晚宴。出席這場晚宴的是幾位歐美財經貨幣政策的最高負責人。在晚餐上,大家討論的一個主題就是當時最關心的次貸危機。其中一個問題是:30年以后,人們會不會記住這場危機?討論的結果讓我感到非常驚訝,他們普遍認為,30年后人們基本上會忘記這場次貸危機;這次危機頂多只是將來大學金融教科書里面的小專欄而已。
當時我和伯南克臨位而坐,我問他,你何以對此有這樣的信心?他的回答是:我們對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原因非常清楚,不會犯同樣的錯誤;我們對拉丁美洲債務危機情形非常清楚,不會犯同樣錯誤;我們對1991年之后日本房地產、股市泡沫破滅,經濟長期蕭條的原因非常清楚,不會犯同樣的錯誤;我們對東亞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也非常清楚,不會犯同樣的錯誤。我反問他,回顧他所談到的每次危機,確實,我們對這些危機發生的原因都很清楚,不會犯同樣錯誤。但是,由于危機觸發的原因都有所不同,我們如何保證這次危機沒有其他意想不到的因素,使其成為一個巨大的危機呢?當時在座的世界經濟的領導人們對此一笑置之。
三個星期之后,2008年9月,次貸危機演化為全面的金融危機。我認為,這場危機的爆發,整個西方世界對此幾乎是毫無準備的,而且可以說是未預期到的。被稱為“末日博士”的魯比尼,由于在次貸危機前預測了危機的爆發而聲名大噪,我卻認為他是瞎貓碰到了死耗子。他說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會引發美國、全世界的危機。他的預測機制是,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后,大家對美元失去信心,大量拋售美元,從而造成國際經濟大混亂。而我們看到的情況是,美國房地產泡沫后,美元地位不是減弱而是加強了。所以,我并不認為他真正地預測到了這場危機。對于危機機制的認識是重要的,因為認識的不同,開出的藥方也就不會一樣。
當9月份危機發生的時候,作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我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幫助世界銀行制定發展中國家的應對措施。這個應對措施在內部有很大爭論,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于這場危機持續的時間,以及因時間長短所需采取的不同措施。當時普遍的看法是,這場危機最多會持續三個季度到七個季度。因為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發生在發達國家的危機最長的也就是七個季度;尤其是經過20年的“大緩和”,對金融貨幣政策的運用自如,時間不可能超過七個季度。如果危機持續時間在七個季度之內,當時他們提出的辦法就是應該使用“自動穩定器”。也就是,危機過程中政府的收入會減少,失業增加,財政支出增加,經濟增長速度會放慢,所以政府就會有赤字,而這個赤字本身就是一個自動調節器。
當時我開玩笑問他們,會不會像圣經里面說的,跟隨七年豐收之后的是七年的災荒,這場危機的持續會不會不是七個季度,而是七年?當時大家都認為我太悲觀。但是,我認為危機可能曠日持久難于擺脫,“自動穩定器”遠遠不夠。政府應該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用于在短期內創造就業、創造需求,長期內能夠增加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率的項目上。2009年2月,我公開提出,為了走出這場危機,應該有一個全球的“馬歇爾計劃”,在全球增加基礎設施投入,以幫助發達國家走出這場危機。人們在當時對這一看法普遍持保留態度。
另外一場辯論是在2010年10月份。通過20國集團采取協同刺激措施,且各國都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世界經濟在2010年上半年出現了“復蘇的綠芽”(green shoot)。據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0年秋季年會時,建議那些受危機困擾的國家退出積極財政政策,通過緊縮財政、減少赤字,恢復民間投資和消費的信心。他們認為,發達國家如果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政府負債會增加,進而會影響民間投資的信心,經濟復蘇前景渺茫。
而我的看法卻恰恰相反,我認為如果政府退出積極財政政策,目標是減少政府的公共負債,但結果可能會適得其反。我當時指出,這樣的政策可能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增加,財政赤字反而會激增,給經濟復蘇蒙上一層新的陰影,進一步降低民間投資的意愿。這一擔心不幸再次被證實。我當時提出財政政策的重點不在于如何減少短期赤字,而在于提高政府財政支出的質量,使其在短期能夠創造需求、增加就業,在中長期提高生產率、經濟的增長率和財政收入,實現中長期的財政平衡。這個觀點在2011年秋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的主要政策方向。
全球失衡的根本原因
從這些經驗來看,我認為,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在發達國家是沒有心理準備的,而發生之后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不到位的。我在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位置上面對的最艱難的問題還不是這些爭論,而是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的爭論。我們都知道,在這次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之前,國際收支有一段時間處于不平衡狀態,美國的貿易逆差急劇增加,中國貿易順差和外匯積累急劇增加。在這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后,國際上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說法,認為這場危機產生的原因,是中國和東亞某些經濟體通過貿易順差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然后用這些儲備去購買美國國債,壓低了利率,從而導致了房地產泡沫,泡沫破滅以后,就出現了2008年的這場全球金融危機。
也就是說,不管是在學界還是理論界,在國際上有相當多的人認為,這場危機產生的原因是國際收支不平衡。按照他們的認識,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東亞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產生了大量貿易順差;二是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后,東亞經濟體吸取了危機的經驗教訓,為了自保,積累了大量外匯,而要積累外匯,就必須增加出口,從而創造貿易盈余;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們認為人民幣幣值嚴重低估,造成中國巨額貿易順差。也就是東亞,尤其中國,是這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這些假說在理論上都是說得通的,但它們與經驗證據是否一致呢?
作為首位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而且是來自中國的經濟學家,當我同別人就此問題進行爭論時,總被認為是在為國家利益辯護。如果進行認真分析,這些說法的內部邏輯似乎是自洽的,確實可以建立一個理論模型,并根據這個理論模型推出那樣的結論。但與經驗事實是否相符卻值得商榷。
首先,東亞經濟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采取了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戰略,至今已經推行了超過半個世紀。事實上,一個可持續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戰略,并非建立在不斷擴大貿易順差這一目標的基礎上,這一戰略的立足點其實是融入國際市場,從而使進口和出口都實現增長,并在貿易部門創造比以往更優質的就業機會。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一進程成功地使東亞地區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同時貧困率也被迅速削減。特別是在2000年之前,東亞經濟體的貿易收支其實是大體平衡的。因此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戰略,不可能是導致2000年及之后全球嚴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第二,如果說國際貿易不平衡是東亞經濟為了積累外匯而“自保”所導致的結果,那我們如何解釋發生在日本和德國的情況?因為對于日本和德國這樣的國家而言,它們的貨幣是儲備貨幣,完全可以靠印鈔票來支付各種需要,因而并不需靠積累外匯來自保,但2000年后,它們的貿易盈余增加的幅度和速度也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相當。同時,1993~1994年,日本的外匯儲備只有1000億,到2006年,其外匯儲備也急劇增加到一萬億美元。當然這一數值比中國要少,但是增加幅度很高。這些完全沒有自保需要的國家,外匯儲備何以增加如此之多?可見這一理論同樣不具有說服力。
第三,將責任歸咎于中國則更為奇怪。認為人民幣幣值低估,最早是2003年春季由日本提出的,當年秋天,美國也加入這個“大合唱”。眾所周知,2003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比1997、1998年還要少,而在1997、1998年,整個國際社會都認為中國的貨幣幣值是嚴重高估,而不是低估。那么,為何貿易順差變小,反而認為幣值嚴重低估呢?而且,中國直至2005年才出現較大的貿易順差,而那時美國的利息已經升高。如果說中國利用人民幣幣值低估來增加出口競爭力,從而賺取了更多外匯,那么相應地,其他同中國競爭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順差就應該減少,甚至變成貿易逆差,且其外匯積累也應該減少。但我們看到的事實是,不僅中國的貿易盈余在增加,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盈余都在增加,而且大部分國家的外匯積累也都在增加。2000年,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累加尚不到1萬億美元,到2007年則已經增加到5萬多億美元。發展中國家自己不能印外匯,如果說中國把外匯都搶到自己國內來,那其他國家就應該減少外匯,為什么反而會大量增加呢?這跟經驗事實是完全相悖的。
上述三種假說都暗示,是東亞經濟體在推動全球經濟的失衡。然而,這條故事線并不符合基本的統計數據。雖然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大幅增加,但美國對整個東亞經濟體貿易赤字所占的份額卻在顯著下降。
上述三種理論如果是邏輯自洽的,不管哪個,或者哪幾個是真的,東亞經濟在美國貿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都應該是增加的。但事實是,1990年代,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中國等東亞經濟體在美國貿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是51%,也就是說美國半數以上的貿易逆差來自東亞經濟體。從2000到2008年,東亞經濟體在美國貿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從51%下降到38%(見圖1),這樣來看,造成美國貿易逆差增加的東亞經濟體在其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反而變小了。所以,雖然國外、包括國內的很多人都接受了以上三種理論,但這些理論同經驗事實是完全不相符的。一個理論如果真能解釋某種現象,不僅其內部邏輯必須自洽,且其推論也應該與所看到的所有外部現象相一致。而這三種理論同外部現象卻是矛盾的。
發生這場危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個人認為根源在美國。眾所周知,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推動金融自由化,允許各種金融機構進行創新,導致了高杠桿。而高杠桿也就意味著允許商業機構創造貨幣,創造流動性。過去五塊錢只能作為五塊錢進行放貸,現在卻可作為十塊錢、甚至二十塊錢進行放貸。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格林斯潘為了避免美國經濟可能出現的蕭條和衰退,對利率進行了大幅下調,18個月連續降息26次,從2001年的6.5%急劇降至2003年的1%。在低利率高杠桿的狀況下,帶來了過度的風險投機,導致美國流動性過剩,進而在住房和股票市場上出現泡沫。這些泡沫的財富效應以及金融創新,允許家庭將其在房地產市場獲得的財富增值進行套現,導致美國家庭過度消費。由于美國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并沒增加,但財富增加,通過套現增加消費使得家庭的負債急劇增加。連同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所增加的公共債務一起,美國政府從克林頓時期的平衡預算變成巨額的財政赤字。民間的過度消費、政府的過度消費,自然導致美國貿易順差的急劇惡化。
美國之所以能夠將這種貿易逆差急劇惡化的情況維持如此長的時間,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元是儲備貨幣,美國可以靠印鈔票來支付其購買行為。由于這種高杠桿、低利率,也鼓勵了很多短期投機行為,不僅造成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股市泡沫,同時也鼓勵了大量投機資本的外流。2000年,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流入的資本是2000億美元,到2007年已經猛增至1.2萬億美元。產生的結果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產生了過度消費和股市、房地產泡沫,另一些產生了過度投資,當然也必然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繁榮。
但是,發展中國家不管是通過經常賬戶賺取到的美元,還是通過資本流入賺取到的美元,在國內都是不能流通的,只有變成中央銀行外匯儲備,兌換為本幣才能在國內使用。中央銀行如果將取得的外匯存放在保險柜里是沒有任何回報的,所以必然結果是,央行將這些外匯拿去購買美國國債,或者進行一些投資。現在國際上流行的說法是,這些國家用外匯去購買美國國債,但他們沒有看到的是,這些外匯都是美國通過印鈔票購買東西和作為外國投資流動過來的。我的看法是,如果在2003年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的苗頭時,美國學界、政界、理論界能夠很清晰地看到問題的根源,而不是委過于人的話,也許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可以避免,至少其危害程度能有所降低。